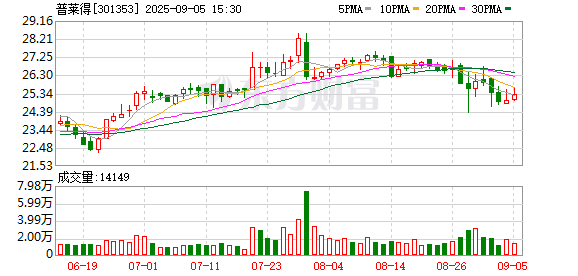天天配资 或许它才是今年最适合大银幕的电影
 天天配资
天天配资
深潜于意识的断裂处
——在感知的末端零距离放大《攻壳机动队》的知觉系统
作者:
Acchan(豆瓣同名)
一个努力争取不做谜语人的迷影人
简目
一 前言及本文立场
二 眼睛:作为意识断裂处的通道
1 身眼的二分-眼睛的特殊性
2 用眼睛捕捉动画的真实性
3 用眼睛打开意识断裂的违和感
三 于意识断裂处的三次深潜
1 第一次深潜:素子的诞生
2 第二次深潜:思维和感知的交织与互置
2.1 前半:从身体的在场到思维的倒灌
2.2 素子的战斗系统:遮蔽眼睛而交给身体的合一
2.3 后半1:傀儡师的新生
2.4 后半2:“我”与他者的对视
2.5 后半3:从眼睛/意识/思维的“看”到身心的感知
3 第三次深潜:死与新生
尾声
“电影无数次地直视草薙素子的眼睛,那双几乎不会眨眼的机械之眼带来的反身性,和我们长久地直视镜中自己的眼睛是相同的感受。纯粹的自我疑难,从眼睛挑起的主体性的违和感开始,延伸至身体部件的颤动,最后汇聚至“灵魂”的显与隐。”

一 前言及立场:对感知的呼唤
《攻壳机动队》(下简称《攻壳》)的文本主题自然是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以来的心灵哲学探讨,后日这类身心二分的二元论被哲学家赖尔批评并嘲讽为“The Ghost In The Machine”,以示二分的荒谬,历经传播,也就有了“Ghost In The Shell”的正式作品命名,日本汉字命名的“攻壳机动队”不过是发行方为了满足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趣,绕开了原作者士郎正宗和剧场版导演押井守对原命名的坚持而特意选取的。
尽管我们在承上的《银翼杀手》和启下的《黑客帝国》中也都会见识到一系列心灵哲学主题的纠缠和延伸,但这并不是《攻壳》作为动画的重点,心灵哲学作为学科的发展已然可以应付大多问题并建立有效的思考入口。例如,电影中有两段最为直接的文本展示:素子对巴特讨论何为自我,傀儡师则发问科学家何为生命。
关于自我,心灵哲学的专业路径会把它分解为多个核心问题:同一性问题,主体性问题和主-客体的边界问题;关于生命,心灵哲学联通生物学哲学,亦创造了不少的理论图示,傀儡师认为“自己是信息海洋中诞生的生命”的观点,和当下由比较新近的“整合信息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IIT)”一致,该理论认为,衡量生命体的关键在于,判别其是否具有高度的信息整合能力,生命的核心,意识,便是信息整合的产物。
本文无意于进一步深入讨论复杂的哲学命题,如前所说,这并非《攻壳》作为动画的重点。本文在意的是,我们到底通过它的感官呈现,在更微观的层面具身地知觉到了什么。本文所有的论述和分析,都旨在召唤这样一种流通颅内和身体末梢的体感,或者说一种精神触觉。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阐明本文立场。本文不作常规意义的文论分析,不是一个结构主义式的透视仪,也并非一把批评和惩戒的意识形态戒尺,更不是冰冷的意义翻译机器和科学研究实验,这些都已经被说得太多。本文仅仅是一个“感知放大器”,并不会凌驾于作品之上,涉及到的一切概念意义也都处于感知的浸泡中。
本文关注的核心是一个更微观层面的知觉过程,旨在最大程度地张开作品自身的裂缝,同时打开我们最小单位的感官末梢,以带来最大程度的丰满且绵密的观影体感。尤其是能有幸在大银幕一睹《攻壳》的视觉魅力,感受这份贯通颅骨和经络的沉浸式表达,恐怕也唯有大银幕能完全唤醒这份独一无二的具身体验。
二 眼睛:作为意识断裂处的通道
1 身眼的二分-眼睛的特殊性
让我们回到动画作为视觉及叙事形式本身的角度。我们首先会发现,同样都是展示文本的智性时刻,傀儡师和素子的姿态却不同。傀儡师致力于辩论的压制,急迫于为自己的存在划定锚点,概念为先;在船上面对巴特那一幕,素子则并非出于话语权的争夺,而是传递刚刚历经海底深潜带来的身体感知,并不囿于概念的辨夺。换句话说,素子是从自身意识出发,和外部世界产生勾连与反馈。
而整部电影,就其能量流动而言,可以说天天配资,就发生于素子在自我意识断裂处的潜浮,这起于一个模糊的感知过程,而非思辨推演的逻辑过程。我们恰恰需要抑制后者的诱惑,下沉身体,解放意识,才能进入素子的意识,以及进入整个电影的维度。
《攻壳》不同于《银翼杀手》和《黑客帝国》等同类作品的本质在于,它位于意识动摇的起始处,位于自我原点的好奇渐渐浮现至整个身体外部的过程中,“我”首次通过眼睛-视觉,意识到“我”的概念,且每一次也都是首次。(根据《攻壳》这套知觉系统,以下出现的“我”,均指的是观众的眼睛/意识和素子的眼睛/意识及电影的眼睛/意识这三者相互重合叠加的“三位一体”,并非完全一比一地绑定,依据具体情境互相游动,重心有所倾斜)
电影无数次地直视草薙素子的眼睛,那双几乎不会眨眼的机械之眼带来的反身性,和我们长久地直视镜中自己的眼睛是相同的感受。抛开社会环境的背景定位,纯粹的自我疑难,从眼睛挑起的主体性的违和感开始,延伸至身体部件的颤动,最后汇聚至“灵魂”的显与隐。
在赛博世界里,这份从自我原点而来的好奇,就如同病毒的传染性和药物的成瘾性,使得自我直视总会抑制不住地突现于任一的认知活动中。慢慢地,我们会发现,眼睛在《攻壳》的视觉性构成中占有的特殊地位,远远大过身体。以至可以说,素子的眼睛和身体是分开的,在身心二分之前,是身眼的二分。
直观而言,傀儡师和素子的最大共同点,也在于他拥有和素子一样的眼睛,则首先就从动画设定的物质性上共享了同一存在性(电影中的设定是,素子和傀儡师的义体来自于同一科技企业)。
没错,眼睛是《攻壳》这个信息深渊世界观的入口,是其中人物/物质存在性的首要衡量标准。除了主角和“反派”拥有这样突出的电子义眼,现身的其他义体人,多以无眼眸的机械眼睛为特征以作区分。相对的,并无完整机械义眼且同时被控制意识的人类,也会着力凸显肉身眼睛的存在——眼皮被尽力撑开、眼白包裹住瞳孔,如被植入虚假家庭信息的垃圾工,以及随之现身的那个“恐怖分子”,他们眼睛的异样首先替代了身体的义体化特征。
2 用眼睛捕捉动画的真实性
一个区分眼睛重要性的边界在于,《攻壳》呈现的是一个还未完全被思维取代眼睛的赛博科幻世界观,无数的决策和信息上演于这个首先用眼睛这一默认的信息输入装置来确认的现实世界。比如,它故事的力量构成来自押井守作为日本人的本土政治认知,及其带来的政治角力的繁复趣味。(在押井守的《机动警察》里,这份上下角力的趣味得以最大程度地彰显。)
这一切角力上演的速率和拉扯的力矩,绝不是游走于个人迷思的《黑客帝国》所能替代的。《黑客帝国》落在缸中之脑的认知困境显然不是《攻壳》所渲染的疑难,我们的一大部分注意力,都在红蓝药丸造成的真假分支上,以及判别这个叙境化空间的真实感上;相反,我们不会指认《攻壳》世界观中这些政治角力是否虚假,而正因为位于背后的无形之力的操控和碰撞,我们才会察觉到它不可辩驳的实在质地。(除了《机动警察》,我们也可对比感知庵野秀明的《新哥斯拉》,同样以政治角力为叙事基底,是充满真实质感的相互关系,而非仅仅是舞台剧式的权力的自我表演)。
甚至有一处情节可看做是专门对缸中之脑的怀疑链表示了实用意义的拒绝:巴特问课长,你怀疑过给你做接入改造的电子脑医生吗,课长回答说,电子脑医生有其专属的心理评估师,当然评估师也是人类,怀疑无止境,只会带来无法解决的不安。
对《黑客帝国》这一建立在数字特效上的电影而言,虚假和真实天然地一体两面,虽然它是真人作品,但我们总是默认了电影是对虚拟的创造,因为它天然地真(摄影素材的真),才能够完全证实它的假的有效性和正当性。
《攻壳》恰恰在极力塑形肉体的质感以追求视觉的真实性,因为动画的假,天然就是“不正当”的,(日本)动画创作才总是不得不需要极力再现现实的真。《攻壳》的作画监督冲浦启之正是以“人肉打印机”的戏称扬名,他和同样擅长写实系作画的黄濑和哉一同贡献了《攻壳》独特的写实主义视觉风格,我们从中感观到的甚至是比真实更为真实的那股粘滞感在视觉成像中起作用,真实到把每个瞬间都足以凝固的程度(实际上这是动画的关键帧机制造成的视觉错觉)。
因此《黑客帝国》无须眼睛的参与,无论是角色的眼睛-叙境化空间中的信息输入,还是观众的眼睛-运动图像的知觉系统,两者都已然从根上被“欺骗”(尼奥的固有形象恰是被墨镜遮挡了眼睛),我们是直接靠意识本身的参与来确定意义的范围和维度,眼睛看到的真与假不具有相互拉扯的张力。
而《攻壳》则会完全调动眼睛-观看的辨识力去感知它所呈现的真实度,小到表情纹路的微动,大到肢体的挥舞和运动形态,再到机械装置的展开和收束,以及城市群的环绕和伫立,每一个元素的显现,都伴随着一次体察真实感的敏锐跃动。形式风格的真实度,和叙事层政治角力的真实度紧密相连,互为表里,这决定了《攻壳》作为动画的基本存在性。
相比之下,我们不会也无需去感叹《黑客帝国》在这些基本素材层的真,不会在意尼奥走路的姿态、抬手的速率、转头的幅度是否具有真实的质感。对于《黑客帝国》,写实是一种内在的自然基底而非外在的形式风格,我们关注的层面起于事件的真与假,属于意识层的认知。对《攻壳》真实质感的辨识则起于写实主义(真实系作画)本身对(日本)动画而言的特殊性,反馈于前意识层。
由此我们可以综合地说,《黑客帝国》是关于虚拟与真实互相变幻的体验,而《攻壳》不是,它的体验在于真实析出并产生动摇的那一瞬。在这一瞬来临前,和我们的感知系统打交道的,是无数次唤起真实感知的演出场景,无论是作画风格的质感,还是政治角力的复杂性,均是为此服务。此刻,我们大加感叹《攻壳》动画质感的真,同时,又从这份真当中看出了模糊的质疑和犹豫。
(若再把《银翼杀手》放进对比的序列,那么《黑客帝国》和《攻壳》反倒在视觉反馈上同属一个层级了。尽管这里说,相对《攻壳》,《黑客帝国》无需“眼睛”的参与,但数字影像制造的思维穿梭终归是落在了更细微的具身反应上,而《银翼杀手》因年代所限,更为抽象古典,视觉只是装饰,并未打破根基的叙境化策略,它靠的是更为形上的诗意固定并区分自身。)
3 用眼睛打开意识断裂的违和感
作画风格愈发追求肉体感官性的真实度,意识游离至边界而对自我概念投射的违和感则愈发凸出,更不用提,某些时刻在这层真实之上附加的变形效果,更是从反方向加强了真实感的提炼,例如。极端的仰视镜头、起于物理轨迹却又超出它的动作场面、飞机的巨大成像和城镇的对照等等,独属于动画性的处理。
唯独眼睛不参与进对肉体的真实性塑型,肉体被动画化(anime化)赋予“灵魂”,但眼睛却反过来被剥离了“灵魂”。由此,素子的真实肉体又总显得陷入了某种缺失,犹如处在人偶和肉身的间离状态,也仿佛身体在场,意识却不在。抽离来看,就像是,一副高精度的肉体,安上了一对不具生气的鱼眼or鸟眼(鱼和鸟是押井守最爱的两种艺术意象),眼睛之外,如此丰盈,眼睛本身,却又如此冷冽。
可以说,整个动画所笼罩在意识断裂处而蓄势出窍的违和感,就建立在这样的冷冽气氛上,眼睛便成了意识在场与否的交界口,也是(经典认知主义的)意识和(新认知主义的)前意识之间的临界点。
如前所述,当我们长久地直视镜中自己的眼睛时,自我的疑难冒头,我们便从这个与我们合二为一的、无须质疑的敞开的经验流中抽离而出,一个“虚幻”的主体性悬浮于我们上空,吸引着我们的眼睛浮出经验之海的水面,直视它的存在。继续往前迈进,当视线位于主体的对面而直视主体时,被给予我们的感知并非是对虚拟性的全盘接受,即立马怀疑主体的真实与否,而首先带来的是一种超真实的感知失调,是越过真实的超真实施加的感官“惩罚”。
更进一步说,在《攻壳》的赛博世界观下,我们和素子的眼睛共同知觉到的是,那份违和感,即意识的断裂,并非来自于任何文本意义和视觉意义的虚假性的冲击(缸中之脑),而是起于信息海洋的感知过载*,是真实的太多,而非真实的不足。继而为了逃离过载的压力,不得不把“我”/身体抽离出来,试图位于上空俯瞰整个信息流。
*电子义眼几乎可以看到一切,绕过任何经验的局限性,以及联通更为广泛的,摄像头、监视器、透视仪、电视荧幕、追踪所示的3D荧屏、地图展示器、装甲车的探视头、狙击枪瞄准器,这些眼睛同时作为素子眼睛的同分异构体而存在,看似赋予了眼睛超知觉的神力(细微地看,宏观地看,透视地看,抽象地看,远距离地看,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实则是对感官-身体系统的全方位屏蔽,眼睛取代了身体,信息流被去身化。
顺着这条观看路径继续往前走,我们会发现,整个《攻壳》的视觉能量的流动,恰好形成了两股相对的层,一股是这些人眼之外的科技之眼串联起来的硬化的地质层,来自上位者的符号位格(无形的政治角力),脱离个体维度的身体,大张旗鼓地彰显科技和权力合谋的神力,这是绝大多数科幻作品都会着力刻画的场面;另一股力量则属于身体末梢反馈带来的微观的感官交互,来自素子和她的眼睛共同构成的凝滞时刻(本文会多次提到这样的时刻,属于《攻壳》的核心),与自我对视的反身性在起作用,质疑科技的判决,且试图穿透这信息流(影像在叙事层的信息交互),把握到别的什么——既属于肉体的可感且可知,也属于灵魂的可感而不可知。
三 于意识断裂处的三次深潜
然后,让我们回到试图飞升上空俯瞰整个信息流的冲动。遗憾的是,“我”终究无法真的占据上空那个明确的端点,而是在前往俯瞰之位的途中,不断地受到这个世界/信息浪潮的引力,把“我”拉回海洋中。于是,“我”总是处于是其所是和是其所非的二象性,受困于“我”被海洋淹没和“我”独立于这个世界的拉扯,在断裂处的两边来回摇摆,用前语言的身体性发问,“我”位于何处,意识位于何处,身体位于何处。(而象征界的语言只能发出表层的感叹,却无法和那个悬浮在上空的虚幻主体性产生的引力精确接轨)。
这便是素子在整个电影中呈现出的姿态,一种表面看去接近沉思的姿态,却并非调动抽象逻辑认知功能而来的有意识的思考,而是被吸附过去,被动地“颅内发酵”。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她被《攻壳》这套动画-电影-赛博世界观强制赋予的姿态,并非发生在可意识的现象层/叙事层,而是发生在前意识的亚现象层,是现象之外的无形之气韵,是叙事之外的那些凝滞的时刻,趋向于静态的、在内部发生的(交合的)、无法轻易被线性时间略过的时刻。
在影片中,这个姿态有一个外显的形态,也就是素子没入水中的那段“深潜”,这里就把其姿态统一称为深潜。《攻壳》的整个影像在现象层/叙事层之外正是由三次深潜所构成,以及那些意识短暂出窍的“假寐”和定格、即电影无数次地直视素子眼睛的凝固姿态,填充了每一次深潜之间的缝隙,以无缝覆盖整个观看行为所获得的具身反馈——那样一种唤醒身体力量的情动时分。
这三次深潜在意义系统的结构上则分别对应草薙素子这具肉身与灵魂的诞生/重生、思维/感知、进化/融合,而眼睛,正是每次深潜联通内外的入口。
1 第一次深潜:素子的诞生
第一段深潜发生在开篇,也是那段留名动画史的草薙素子之诞生。伴随光学迷彩的开启,素子的身体逐渐隐蔽,仅剩面部和眼睛,最后,已经隐形的左手略过面部,完成了整个身体的隐形,同时,电子音效的电流嗡嗡声唤醒了妖异而原始的主题曲傀儡谣,亦完成了声觉上的交接。(图 1)

图 1
我们穿越素子直视镜头的眼睛,来到了抽象的虚拟电子世界,此时银幕被绿色电子线路占领,电影标题“Ghost In the Shell”显现。随即,我们又进入到机械躯壳正在装配的直观的实在物质世界,接下来,两个世界相互交替,逐渐创造出草薙素子的完整身体。(这里说虚拟电子世界和实在物质世界的对立,并非基于科学语言,而是一般意义的语言,科学观下,一切基于物质,无需二分)
本文开篇提到,“Ghost In the Shell”的命名源头,来自赖尔批评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而导致的“The Ghost In The Machine”这一荒谬结论。在心灵哲学史的路径上,赖尔所处的正是一个生物学/医学牵头,以唯物主义/物质主义为基础大举取消非物质占比,攻占心理学的时代,笛卡尔时代以来的身心二元论,首先被限定为基于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物质是一切基础也是唯一实体,没有精神/心灵等第二个形而上的实体,二元论是荒谬的。
《攻壳》取此命名自然并非出于批评之态,相反,身心二元论带来的灵肉对立的基调才是《攻壳》着重呈现的,这首先是它的艺术属性决定的。因为《攻壳》作为艺术品,首先面对的是感官和知觉问题,无论心灵哲学作为学科在概念上和科学实体的演进上如何有效回应了二元论疑难,都无法取消这些疑难本身引起的心灵感知,哪怕它在概念上和实体上和语言上被定义为“认知错觉”,恰恰在感官-艺术-表达这条肯定内倾感知的人文路径上是绝对正当的。
回到第一次深潜,这一身心对立的基调早已蕴藏其间。首先,标题“Ghost In The Shell”的呈现,正好是中间的“In the”先出现于银幕,然后“Ghost”和“Shell”分别从“In The”的两端同时浮现,已然暗指了两者的二分和对立(图 2);随后,物质世界和电子世界相互交替,“Shell”即素子的躯壳来自物质世界,而素子的“Ghost”即灵魂则来自电子世界。

图 2
(剧情中,角色们口中的英语“Ghost”一词实则指用来产生意识的那套被制造出来的系统机制,而角色口中出现的日语“たましい”,日本汉字写作“魂”,读作ta ma shi i,才指我们一般意义上带有形而上属性的所谓“灵魂”,这里我们从标题出发宏观看待“Ghost”一词的意谓,即一般意义的那个形上用法,而非剧情中的指涉)。
因为我们会发现,紧接着机械躯壳出现的,装载灵魂的大脑,并非显现于摆弄机械装置的物质世界,而是由电子世界的虚拟图像构成(后面扫描傀儡师时,也有用虚拟的透明3D电子图像显示傀儡师的脑组织)(图 3),同样,随即出现的整个外显的人形(人的气韵),也是由虚拟图像显现。

图 3
脑-灵魂给非物质,躯壳-身体交给物质,完美的身心二元论。但笛卡尔处,虽逻辑上称其为身心二元,灵魂-精神(心)却在暗地里高过身体-物质,这也是笛卡尔的基督教信仰所致。
相同的,在身心二分的基调下,《攻壳》也偏向于承认灵魂位于更高位*,这也才决定了素子那双眼睛的意义,才决定了素子不断直视自我或者被电影所直视的凝滞时刻,必定是有那个“灵魂”在先,我们才会陷入自反性的凝滞时刻,才会被素子的眼睛吸入其中,和素子一起,在意识的断裂处动摇。
*一个有趣的视角是,第一次深潜的电子世界中,除了电子虚拟图像呈现的脑部和人的外形之外,还有翻腾的绿色二进制构成的制作人员表,这何尝不能暗指灵魂的优先性?素子的灵魂甚或于动画的动画性/灵魂性(日本语境下动画所称的“anime”一词来自拉丁语“anima”,意味灵魂、生命)正是创作人员所赋予的。(图 4)

图 4
第一次深潜,是全身心的解离,在灵肉(身心)的开始,便埋下了无法调和的断裂。(比视觉更为突出的特征必定是伴奏的傀儡谣,那样一种呼喊灵觉,唤醒沉睡的灵魂般的歌声,让整个物质世界都黯然失色。)
第一次深潜即素子诞生的末尾所接的下一个镜头是躺在床上的素子睁开双眼,没有丝毫肉体所感的睡眼朦胧,充满质感的双眼蓦地张开,形成了一次新的直视(横躺的直视,后两次深潜均出现了同样横躺着的直视,形成对照)(图 5),仿佛在睡梦中经历了那样一次深潜,位于意识断裂的余韵里,还未完全回过神来,眼神定格,指尖承接着余韵而微动。

图 5
接下来,素子的身体没入日常秩序,起床、开窗、穿衣,但这份来自断裂处的余韵继续扩散,(此时傀儡谣的乐器-鼓和神乐铃也余音环绕),实际上使得她并未完全投入日常秩序,而是透过窗户,与外界隔离,窗户正如同眼睛的放大器,透过外部世界的光亮射进眼中。“我”则在内部世界的黑暗中,意识到我在使用“眼睛”和这个世界对峙,“我”在意识断裂的边缘,观望这个世界,而非沉没于这个世界(图 6)。至此,第一次深潜结束,视角来到外界叙事层的政治角力,开启正式情节。

图 6
2 第二次深潜:思维和感知的交织与互置
2.1 前半:从身体的在场到思维的倒灌
第二次深潜由前后相邻的两部分构成,前部分是字面意义上的深潜。在与恐怖分子战斗后,素子独自一人乘船来到某一近海区,把自己抛入水中,深潜下去。如此描述基于事件的因果关系补充,而这一段实际的视觉感知效果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素子先从水中的深潜“苏醒”,再缓慢浮出水面。进入水中的通道,仍然由对素子眼睛的直视开启。
镜头回撤到入水前的上一幕,素子隔着审问室的玻璃窗观察被捕者,玻璃窗反射出素子的身影和眼睛。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素子看的并非被捕者,而是自己的玻璃倒影,背景台词正好配以对自我意识和同一性等话题的探讨;随即,镜头切换至玻璃窗内,反过来正对素子和她无神的眼睛,镜头隔着玻璃窗,色彩发生偏移,变得阴冷,随着水泡模糊景象,阴冷逐渐加深,正好接续阴冷色调的水中场景,对素子眼睛的直视再次打开了通往意识断裂处的通道。(图 7)

图 7
素子浮出水面的整个过程,则是从蓝色冷色调的深水区,逐渐上浮至颜色渐次柔和的浅水区,接近水面时,我们才发现这是由于夕阳时分的暖色调透过水面调和所致;临近水面之下,素子的整个身体又反射出了一道倒影;继续靠近水面,实身和倒影逐渐重合,最后浮出水面,倒影被打破,实身漂浮于此(图 8);然后镜头给到素子睁开的眼睛,素子转动头颅,视线给到待候之船。(又一次横躺的直视,这里所呈现的,像是无机质地转动头颅,和结尾素子横躺望向傀儡师如出一辙,以及最后素子的头颅分离,睁眼侧倒一旁,是死亡、也好似未曾死亡,意识断裂。)

图 8
不难感知到,从水面到水上的整个过程,也是素子从意识断裂处的摇摆到回神的过程,水面恰似一道隔绝内外的断面。透明的断面也映衬了断裂处两面的相互勾连,它并非一块突兀的黑洞,而是空出了一片让我们得以凝滞的时空,一个足以让我们产生动摇的过渡态,也就是使素子的姿态得以可能的逐渐降低活性的惰性场。在此处,处理外界信息的感官被剥离,眼睛向内看,意识既游离于外部,沉于模糊,也异常清晰地觉知到内部“我”的所在。
巴特问潜水作何感受,素子并不犹豫,敞开感知,真诚回答说,“我感到恐惧、忧虑、孤独、黑暗,以及浮出水面时的希望”,这恰恰是把身体展开换来的体验。和第一次深潜一样,意识断裂处带来的余韵并未消散,继续环绕其间,回荡起新的知觉。
于是镜头再次对准素子的面孔,以及她的眼睛,并随着素子倾倒思维状的感知体验开始变形,构成了一个鱼眼状的滑动变焦镜头,附带有特殊的动画形变的张力,极具感官冲击性(图 9)。似乎刚刚在深潜中因为位于断裂处而剥离的一切身外信息,又汇聚成洪流倒灌进意识断裂处的通道,“我”被淹没在“我”自身的海量信息面前,深潜“失败”,坠入渊底。直到一个他者-傀儡师的声音,闯入自我意识,被冲散的通道又再度被打开,素子重回外界。

图 9
2.2 素子的战斗系统:遮蔽眼睛而交给身体的合一
第二次深潜的这前半部分,本是素子尝试用深潜关闭眼睛这个特殊的输入感官,从而让纯粹的身体反馈接管意识层。我们能发现的是,临近水面之前,素子是闭上眼睛的状态,正意味着她把自己交给了更原始的身体反馈。如此“交出身体”的姿态和素子在战斗状态时刻意用装置遮住眼睛有相同之处,也是遏制“我”的眼睛/意识,全权交给这具应用自如的战斗“机器”。
虽就设定的逻辑而言,此装置是为了进一步增强素子机械义眼的能力,以大幅提升战斗力,但就视觉的逻辑而言,这恰是对眼睛的遮蔽,对断裂处通道的阻隔,防止“我”的浮现影响身体的运作。我们感知到的那份超越真实的写实主义带来的违和感暂且消失,被转变成更为流畅的运动,凝滞时刻被与它相反的灵活性取代。正如发行方一定要绕过晦涩的文艺哲思,为吸引观众观看欲望而使用“机动队”一词,此时的运动不再为呈现凝滞的时刻作铺垫,而是为了普遍意义上观看的顺畅和刺激,是一种带有强烈目的的机动性。
在素子和第一个恐怖分子战斗的过程中,我们甚至能看到素子那犹如李小龙般的迅猛攻击,似乎是同时为了配合香港背景,镜头也很懂地来了一次三机位回旋踢演出,非常地Hong Kong Classic Style。此时身心二分暂时统一,身体全面接管了眼睛的凝视功能,如功夫理论会倡导的那样,身外一体,没有干扰,一切完全流畅地运行,断裂处的通道彻底关闭,素子身在一个完全外部的世界。
则此时的“看”并非瞪大眼睛直视意识的凝视,而是没入经验之流的“捕捉”,没有“我”的参与,自然也就“天人合一”。在一种基于道家理论的中式逻辑中,反身性的意识恰恰是一种阻碍,没入世界经验之中,没入大道之内才是最上位的追求。(注:这里并非进入了德勒兹意义的去主体性的当代框架,而是以消灭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传统框架)
当然,遮蔽眼睛/意识为了战斗,和在深潜中遮蔽眼睛/意识为唤醒身体触感,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为了“天人合一”,后者恰恰是为了暴露身体的存在,并不“合一”,是为了在信息洪流中拯救属于自我的身体,即素子深潜入海的直接目的。结果却又总是处在矛盾中,即又总是反过来在亚现象层开启了前意识的运转,继而遁入意识的断裂处。身体或许得到了短暂的拯救,自反性的意识却又趁虚而入,激起思维/感知的双重回荡。
2.3 后半1:傀儡师的新生
往后,他者-傀儡师的声音闯入,此刻,素子重回外界。但随即,镜头重新定格至素子回望城市的眼睛,亦直视着素子的双眼(图 10),素子出于搜寻傀儡师的目的,再次进入新维度的深潜。后半的深潜由再次升起的傀儡谣和香港-东南亚风的高密度城市漫游编织而成,一次恰好对立于前半的外部体验,一次自我面对他者的深潜。

图 10
在进入城市视角前,素子回眸的前后一刻,悄然响起两次神乐铃的声音,作为后半深潜时傀儡谣的引入。这个安静而短暂的引入,和第一次深潜的前一刻即素子完全隐身的那一刻(也是标题浮现的前一刻)浮现的神乐铃声一样。
不同的是,第一次引入只有一声,第二次有两声。第一次的那一声铃声前,浮现的是光学迷彩运行时的电子声,是从电子声的嗡嗡作响过渡到铃声,所以唤醒了傀儡谣的同时,也唤醒了素子诞生时电子世界的电流与机械的运作声。第二次的两声铃吟并不直接属于素子,而是引导素子的眼光回望城市方向,指引她前去探索傀儡师何在。
实际上,傀儡谣正是赋予肉身灵魂的一曲召魂歌。歌词中,上古神灵的合夜,既是对后面傀儡师和素子合二为一的指涉,也意指素子的肉体通过祭祀祈祷被(上位者)赐予灵魂,但“新婚合夜”实际上是关于肉体的神圣性,所以也能反过来意指灵魂被赐予肉体。则第一次的傀儡谣,赐给素子灵魂,素子诞生,第二次的傀儡谣,完全就昭示着傀儡师的诞生,他恰恰是先有了灵魂(已然在网络空间出现并作为黑客名噪一时),再被赋予了肉体。
傀儡师定义自己为“信息海洋中诞生的生命”,而错落繁杂的香港街景,从空中鳞次栉比的楼层和招牌,到地面熙熙攘攘的街道,再到水面凌乱不堪的垃圾,正是信息海洋的一面生动写照。(第二次深潜后即城市漫游完结后,紧接着便是傀儡师的登场,裸体湿身伫立公路的镜头,像极了刚从羊水生产而出的婴儿。)
傀儡师的诞生并未如素子一样给予直接的展示,一方面,符合他对自己是信息海洋诞生的生命的定义,隐没于整个世界,无从可见,却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次深潜仍属于素子,是素子来到他者场域探知外部的一个泛意识流的过程,仍然是以素子的眼睛为泛视点,去知觉整个外部世界。
从前半在海下闭上眼睛的自我深潜中走出来,素子的那双眼睛看向了外部城市。一架极度夸张变形的飞机,像肿胀的怪物般扑面而来,极富冲击力(图 11),则不仅是素子看向外部,也宣告着外部世界对眼睛/灵魂的猛烈入侵。

图 11
这一段,是在城镇上空第二次出现的飞机。第一次在街景中出现的飞机大抵是正常尺寸,仅有些微视觉调整,就像我们在《重庆森林》里,从同样的香港街景中看到的掠过天空的飞机。第二次对飞机的感知,则完全是刚从幽暗的水中出来睁眼看开阔处所受到的视觉压迫,不是我们的视线发现了它,而是被它所发现,然后瞄准我们俯冲而来,如同一只骇人的天空怪鸟,想必喜爱鸟之意象的押井守有意处理为此。
2.4 后半2:“我”与他者的对视
然后,视线来到水面,附着船只穿行。水下和水面,完全两个世界。在水面上这个他者场域,这个外部世界,“我”看似随着经验之流飘动,搜寻他者的踪迹,实则仍然在回看“我”,仍然在搜索“我”位于经验之流的何处,只是这样的回看,是通过不断反弹他者的“看”而实现的。
第一次深潜是在二进制和电子电路的信息洪流中塑造肉身,第二次深潜的前半本是为了隔绝信息洪流,唤醒身体的在场即感知,却又反过来引起了信息洪流的倒灌即思维。这里所谓的信息洪流,不过都是抽象的0、1数字,是自我与自我处理关系时,外界流过的符码。但物质性的外界信息,并非能还原为一串抽象符码,而是拥有无法简化的肉身性和物质性。
由此,“我”并不能穿透这一切信息来到虚幻的高位,即俯视的端点,“我”只能位于这之间摇摆,不断地在他者的肉身性和物质性之间碰撞,析出自我意识的违和感。正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有言,“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但这里的他者不只是泛泛于外部世界的芸芸众生,更明确的那个他者正是无处不在的傀儡师,是正在诞生/降临的傀儡师隐藏在经验之流中看“我”。“我”本来是为了搜寻他者-傀儡师而来,却被他者-傀儡师带入了凝滞时刻,深潜于恍惚的意识断裂处。
一个有力的“证据”便是,城市漫游中随处可见玻璃橱窗和各式荧屏,却没有出现一次素子的倒影以打开直视眼睛的通道。要知道,前半部分的深潜正是由审问室的玻璃倒影开启了意识断裂处的通道,再由冲破水面的倒影暂时关闭了它。而此段对眼睛的直视发生在两个素子穿越时空相互对视的场景,相隔于她们的,正好是大厦的玻璃窗,所以她们互为倒影,也互为真身,更重要的是,两个衣着不同的素子(特意用了高区分度的红黄加以区分)互为他者。(图 12)

图 12
就情节的因果性而言,大厦内的素子和水边的素子分别是不同时空下,素子穿梭于城镇各处搜索他者-傀儡师而留下的身影,这里被刻意剪辑成一个连续的时空下同一条轴线两端的对视。霎那间这造成了似乎存在两个素子的错觉,而整个赛博世界观下,因为义体的设定,存在两个素子的事实,又似乎是可以被实现被接受的,由此这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视带来了非常耐人寻味的神秘体验,我们的感官和认知产生了错位,迷失于令人兴奋的危险感。
如前所言,这次对视的发生,正是“我”经由他者的层层反弹之后,由他者开启的,并非由自我开启。正如那一架似巨大怪鸟般的飞机,是它作为他者发现了“我”并试图飞扑而来入侵“我”的眼睛,然后“我”被它巨大的身影撞开,又与别的他者碰撞,如此反复,直到对视的发生,打开意识的断裂处。
乘船从水道掠过期间,虽然“我”面对着万千真实的物质构成的城市,但“我”无法凭借思维穿透它们,而总是在用眼睛/意识在浏览和搜寻,也就是总是处于“看”的隔离状态,未曾真的参与其中。上空盘旋着傀儡谣的神灵,地面蜷伏着繁杂的城镇,意识断裂于此,“我”被夹于其间来回摇摆。虽然身体在行走,意识却仍在深潜,趋于凝滞,一种上升且回旋的凝滞。
和前半关闭眼睛进入的惰性场不同的是,“我”深潜于一个纷纷扰扰的活性场,一切在旋转碰撞,信息的过载致使感官位于临界点,“我”又陷入凝滞时刻,是“我”被过多的外界反馈即过多的他者之“看”挤出身体而带来的凝滞,并伴随着视点从各个方向蔓延开去的眩晕感。所谓信息的过载,不是抽象数据汇集而起超出容量的过载,而是经验之流本身的无数不可被分解还原的实体触感在碰撞着感官。
看看整个香港-东南亚风格的密集城镇和高科技化的钢铁森林之间的区分吧,后者由粗壮的钢筋混凝土构成,高速公路和高强铁壁取消一切的差异性,它们本身就像是电子回路般“简洁”,磨平所有的真实气息。前者是完全活性的,和数字信息相结合,而非被取代。
2.5 后半3:从眼睛/意识/思维的“看”到身心的感知
镜头离开水道小艇,来到岸上的人群,开始仔细刻画常人的姿态,生动的肉体,灵动的狗(押井守的爱狗),举着雨伞等各样丰富的仪态出现。此时,写实主义进入到了完美的再现之态,区分于素子和巴特他们超真实到粘滞的间离的违和感,也区分于素子战斗时“天人合一”的过度流畅,外部-他者-世界如实地存在着,日常如实地运转着;
时而平静——路人的等待,时而躁动——雨点的飞扬,时而点缀惊喜——孩童们自由地奔走,甚至连无机质的汽车的运动轨迹也被灵性地捕捉,纳入整个有机质的生态群,活性场的能量被激发到顶点。此刻的“我”,在意识断裂处看见的竟然不是更深的“我”和更深的质疑,而是坚固的众生(我从玻璃中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倒影,是外界人群的倒影。图 13),是向外构建和整合的能力,终于是全身心的感知而非单一的看/思维发挥了作用,也终于从浏览和搜寻短暂地转变为“欣赏”,参与了进去。这样属于动画的写实,恰恰是绝对的真实,绝不可再被任何程度的缸中之脑疑难所消解。

图 13
这样来看,前半于意识断裂处的深潜,起于眼睛/意识的关闭,意在张开身体,却通达了思维的丰度,后半于意识断裂处的深潜,则起于身体的(被迫)退位,意在用眼睛/意识搜索并辨识信息,却导向了感知的宽度,一个相互交织,互为表里的,联通自我和他者的身心二分,并非原始语境下那个各自为阵,互不连接,相互平行的身心二分,从感官层面完全颠倒了赖尔对身心二分的批评。
漫游结尾,傀儡谣结束,镜头落在了橱窗内的塑料模特上,活性场顶点的平衡被打破,似乎一切有机质的整体,被赋给无机质的模特,灵魂被赋予肉体,则傀儡师诞生(图 14),正好和素子肉体被赋予灵魂的过程相对。

图 14
一个绝对的,和“我”完全平等的他者-傀儡师被创造了出来,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女性)身体、同样的生命意识、同样的怀疑、同样地曾深潜于意识断裂处。则“我”需要从自我意识断裂处被拉回到经验之流中,调动一切意识和这个绝对的他者并行/对峙。(素子对巴特明确说过,自己和傀儡师很像,在最后的融合中,傀儡师对素子说过,“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就像照镜子”)
3 第三次深潜:死与新生
两次的完整深潜,也正好是两次身心的诞生。最后一次深潜正是神灵在新婚合夜的“交欢”,素子和傀儡师互换意识/肉体,既可看作是一次纯粹的意识空间的深潜,也可看作是一次肉体感知的交换,由傀儡师和素子共同完成。素子超越意识的断裂,不再摇摆,来到了新的维度,终于飞升成灵(网络),“进入到更高的境界”(傀儡师语);完全相对照的是,傀儡师获得了渴望的肉体,准确地说他渴望肉体的DNA,渴望肉体作为生命的“功能”,意图在基因层面达到永恒。
但此等永恒建立在个体的限度之上,必定得历经个体的死亡,为了基因层面的永恒,他接受了个体的有限性,看似“大义凛然”,实则充满了“心虚”。因为他终是明白,自己并不具有生命的进化功能,所以最后借着毁坏的生命之树形象,向素子和观众道出了他的诉求和期望,以及导演本人的生命观:懂得自发的进化和生产,才是完整的生命。
所以傀儡师意图和素子合二为一,也正是因为并不满足复制人的空虚和透明——那不过是他所嫌弃的,被称作AI的无意义的单一存在。相反,他从意识断裂处浮现的欲求是,需要生命本身的神秘和不透明,也就是它的复杂和可能性,就像海德格尔在后期所表露的理念,存在的价值需要在“遮蔽”中被体现,也正如贯穿全片的Ghost,那个“我”,左右着一切,藏在暗处,若隐若现。甚至能说是,傀儡师需要肉体/生命,恰是为了迎接它在个体维度的死亡。
两者的肉体各自横躺侧视对方,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正反打,一如伯格曼《假面》的经典构图(图 15)。本已交换身/心的两者通过眼睛的直视,亦再次各自深潜入对方的意识裂缝,形成了一次完整的回环,那个瞪大眼眸的素子即一直位于意识断裂处的素子,终于得到了对等的回应,是他者的回应,亦是“我”的回应。

图 15
此刻,天空洒下轻柔飘扬的羽毛,一个独立于这套冷冽且凝滞的知觉系统的异质性元素,以它完全反写实风格的柔光四射的梦幻感,短暂地占据了画面/眼睛。希望,是素子对巴特所言的希望从天空洒落下来。是的,原来第二次前半的从海中深潜浮出水面的时刻,也是希望带来了暖色调。羽毛的梦幻柔光反射进素子的眼睛里,这双隔绝表情的人偶般的无机质眼睛,似乎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喜悦与兴奋。(图 16)随即,羽毛召唤出天使,迎接两者的新生,及死亡。

图 16
第三次深潜,不仅“完美”跨越了身心二分的藩篱,还借素子之口,铆合了同一性问题:每一刻的“我”都不同于上一刻的“我”,没有那个受限制的自我;最后,当然也“解决”了基于主客关系的他心问题*:“我”不仅触及自我成为可能,和他者的全身心触及亦成为可能。关于自我的几大核心问题都得到了回应,前两次所深潜的意识断裂处经由第三次深潜,均被缝合。跟随素子的眼睛以及“我”的游动,我们犹如一团仅剩神经末端反馈的触须一样地,精微而敏锐地知觉到了从断裂处的徘徊到缝合时的飞升这整个过程。
*一个值得延伸的对比是,日本动画史上(甚至我愿称其为世纪末的影史上)最著名的一幕主客关系的他心问题,在《攻壳》上映三年后的1998年上演于《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剧场动画《真心为你》,遗憾的是,主角真嗣打破主客边界的互融以失败告终。哪怕全世界都融进“生命之水”,唯独无法消融那个绝对的她者-明日香。同素子一样,此刻躺在地上的真嗣也有一个转头侧视的姿态,只是他没有得到明日香同样转头的回应,回应他的,却是自我同一的象征绫波丽的虚像,他最终仍然只能直视自我(图 17)。最后留下的,是他者-明日香对“我”说出的“恶心”,一个绝对的拒斥之态。庵野秀明的世界观里,没有网络来承载他心问题,这并非是个人秉性的局限,试问,当下被网络覆盖的我们,真的不再有真嗣的自言自语了吗?恐怕正相反,网络似乎让“我”对我的直视,无限膨胀。

图 17
尾声
但,能自由融进网络的素子/傀儡师(或者说电影,那个“我”)真的彻底逃离了第三次深潜的意识断裂处吗?这是否意味着,凝滞时刻对灵魂的呼唤不再起作用?肉体也不能隔绝感官的过载单独在场?时间被永冻,边界亦被完全取消?生命真的能完全上交给网络?答案是暧昧的,至少可以说绝非肯定的:一个以偷窥的姿态直视素子/傀儡师眼睛的第三方视角悄然靠近,并唤醒了她-她们进化/融合之后的新身躯。(图 18)

图 18
第三方视角可以是任意装置的“眼睛”(显示器、监控头等),也可以根本无须一个主体的承载,仿佛是在说,既然你脱离了单一的主体而融进了网络,则反身性的直视——“我”也一起融进了无处不在的空间,你无处可逃。素子/傀儡师从高位凝视世界,世界也在凝视TA,凝视那双眼睛。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
天臣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